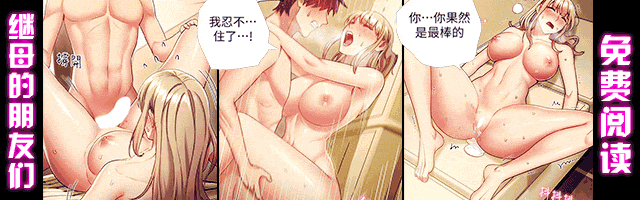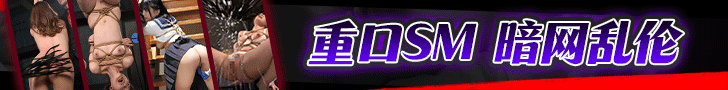坎贝尔他看上去太懵懂了,就差直接问胥寒钰在做什么了。甚至过了很久,等胥寒钰在他体内的抽插都渐渐顺畅,坎贝尔才小心翼翼的说:“我不是雌虫哎……”
“我知道。”雄虫淡淡地说。
因为坎贝尔表现的乖所以胥寒钰动作也一直很温柔。
只要他想,充分的扩张和柔缓的节奏让初次承欢的雄性身体都不会有任何不适甚至感到暖洋洋的舒适感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大概是那样是舒适让坎贝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理解自己被一个雄性侵占的事实。
但到此为止了。
胥寒钰开始大刀阔斧地入侵。
腺体被操弄的时候一直柔柔的少年睁大了眼睛,浅色的睫毛颤抖着宛如要飞离的蝶。
坎贝尔自然不知自己的性腺在肠道的事情,更不知道被雄虫操弄那里的感受。
本来雄虫就不会知道这种事情,在雄雌比例差距巨大,雌虫们又受强力的雌虫本能影响的虫族社会,也不会有雄虫会被另一个雄虫使用的情况。
正常来讲。
所以对于坎贝尔来说这种难以理解的感受和刺激超出了他大脑的承受范围。
被压在原人类身下侵犯的雄虫拽紧了手,指尖摩擦过床榻,在这个战虫都可以制衡的床榻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唯有指尖摩擦得红肿,又因为按压尖白。
坎贝尔是想用手指掐着掌心辅助自己从那样的快感冲击力逃出来的。但还是不够用,当他被撞击到那里,被阴茎摩擦过那里的时候都难受到哭泣,刮挠床榻,好像这样虐待自己的指尖才能把自己从那种恐怖的快感里拯救出来。
他是真的觉得那样的快感恐怖。
和刚刚温水一样的摩擦不同,此时的作为让一直性厌恶的雄虫真正产生恐惧的情绪。
恐惧身体不受控制。
恐惧未知的感受。
身后虫族的肉棒挤入肠道,抵着性腺碾压,蹂躏而过,用自己的阴茎揉搓身下雄性的前列腺,给予前列腺按摩一样的无法拒绝的性快感。
随着性奋不断堆积,一直以来堆砌的感官、委屈、忍耐爆发,坎贝尔被操得崩溃大哭,哭喊着拒绝求饶,哭叫着逃离,然后被身上的雄虫拉回笼罩在臂膀之间,承受雄茎的制裁,被挤压出快感,甚至高潮。
被生生操射。
雄虫高贵的精液没有落入精密的仪器或者雌虫温润的口舌肠道,而是射在了毫无设置的硬板床上。
深色的床,冰冷的材质,坚硬的质地,与射到地面上无易。
此时也不会有雌虫上前舔舐,尽量让雄虫的精液不被浪费。
而是就这样被浪费在那里。
好像被摒弃价值的不是精液,而是坎贝尔整个雄虫的价值。
他射了,他在另一个雄虫身下被活生生操射,而这对于那个雄虫来说完全的不关紧要。
没有理会他射出的精液。
也没有理会他的高潮。
不要说收集精液,刚刚射精的坎贝尔甚至不能得到休息,更甚是还要在这段贤者期间持续地使用和侵犯。
坎贝尔应该感觉难受的,来自被枉顾感受的使用引发的难受。
但他没有。
他可能难受了一会儿,之后就在这样的雄茎制裁下,被插着肠道,获得了强烈的前列腺高潮。
和以往的射精都不一样的,仿佛是射出了髓液一般的快感。
脊椎在颤抖,身体在痉挛,屁股一定是因为痉挛才不受控制地前后抖动,抵着后面的下腹,屁股挤着胯下射精。
也许不是精液。
那白浊的,一点不受这个身体的主人控制的液体。
它们的控制者不是这个身体的主人,而是操弄这个身体的虫。
是身后的雄虫操控的东西。
或者说,被操控的不止是它们。
坎贝尔变得迷迷糊糊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哪里不对。
好像太舒服了,没有一丝不悦。这样的不对。
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屁股里的肉棒是个宝贝,弄得他舒服透了。知道自己的肠道好像有些不受控制,又有点可以控制,知道在对方的大肉棒抽出的时候假紧挽留就可以感受到被扇状沟刮挠的汹涌快感,知道自己的肠道被入侵的时候一点会不受控制地长得大大的纳入对方。
迷迷糊糊间坎贝尔听见自己的声音。
粘腻至极地声音。
啊啊叫唤着。
比他最讨厌的要讨雄茎的雌虫还放荡。